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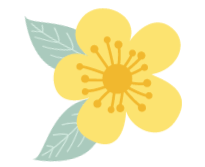

“彩虹!看,在那里。”
“哪里啊?哇!看到了。”
“好壮美喔,黑山的彩虹。”
“还是双彩虹呢。”
庚子初秋的第二天傍晚,一场偏东雨后,我和家人在老家的万盛黑山谷南门户外散步纳凉。只见绿绒绒的坡地草坪上、房前屋后、公路上……,东一处西一处,高高低低都是些密密麻麻的人,他们不约而同朝着黑山方向,有的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有的拿出手机、相机照个不停,生怕错过了精彩的瞬间,满脸荡漾着笑容。
对于生活在具有热岛效应的大城市,在密集的钢筋水泥大楼,川流不息的人群、汽车中,经历了滚烫的太阳烘烤的人们来说,初秋黑山的这场偏东雨,来得太爽性了。斜阳西下那悠悠的蝉声晚唱,合着空中稀稀疏疏的雨点,树叶上晶亮圆润的露滴,溪涧里清清如练的流水,山谷间绚烂飞架的彩虹,真是置身于一幅难得的声色融润、清新悦目的立体童画呵。
听不少人说,当天的万盛城区、青山湖、石林,好多个地方都看到过彩虹呢。
老家偏东雨后的这道彩虹,自我外出工作后就不曾亲眼见过。当然,其间除了四五年戎马生涯在异地他乡外。但心中始终牵挂着她,这一牵挂呀就是二三十年。这次能亲眼看到故乡的彩虹,心情啊就像与久别的至亲相见一样。

彩虹,在万盛民间叫作“杠”。不知道是不是乡亲们“识字读半边”的原故,把“虹”字认成了“杠”。反正大家看到彩虹的时候,都说“打杠了”。在老家只要有涌泉飞瀑的地方,阳光下不分季节都能见到细小的彩虹,但大的彩虹出现一般在秋天的偏东雨后。那道彩虹啊,往往跨度长好几公里远,场面太壮观迷人了。
偏东雨多半在晌午饭后。它跟你从来不商量的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爽爽快快、大大咧咧的。当乡亲们在田野里埋头割水稻打谷子、晒谷坝上来回翻晒粮食正起劲的时候,老天爷恰似小娃儿的那张脸,没哪个得罪他,说变就变了,不一会儿天色乌云密布,风声骤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乡之势。趁着雨足在远处起步的时候,乡亲们大呼小唤的,从这塆喊到那塆、唐家叫到李家,抢偏东雨的氛围一下子就躁动起来了。这在“出门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提醒家家户户抢偏东雨的消息,也算传得够快的。你看那男女老少喔,如螃蟹上树七脚八爪,扫的扫、撮的撮,抬的抬、搬的搬,背的背、担的担.......一派人声鼎沸的场景。等大家刚消停下来喘喘粗气、揩揩汗水的时候,偏东雨在雷鸣闪电的陪伴下大模大样的来了。累了大半天的人们总算找到了个心安理得的歇气机会。因为,老家的偏东雨一般都要过三趟,第一趟,雷电交加,风雨如泻;第二趟,雷电渐弱,风雨如帘;第三趟,雷声隐隐,远去他乡,风雨丝丝;最后,稀稀拉拉的两三点雨滴,疏疏悠悠的四五丝淡岚,在西向的阳光反照下,彩虹就这样盛装登场了。
些许慌忙,偏东雨短暂打乱了乡亲们一天的劳作安排,但风雨后的那道彩虹,无论如何还是带给人以不一样的愉悦的。
彩虹对于儿时的我是神秘的。“为什么秋天偏东雨后有彩虹”,“彩虹为什么像一座大大的拱桥”,“彩虹上面可以走人吗”,“彩虹是不是龙变的”.........。入夜,月明星稀。忙碌了一天的一家老少、左邻右舍,常常端来几个板凳,舀上几碗老鹰茶,围坐在屋檐前空旷的坝子里,用扇子边引凉风边拍打着山蚊虫,漫无边际的摆些东家长西家短、张三李四王麻子之类的龙门阵,或吹吹今天你家我家收割的谷子空壳多不多等等咋咯里咯的寒温。但大人们对白天看到的彩虹丝毫不感兴趣,脸皮厚的我心痒痒的老想着从他们嘴巴里掏出点儿彩虹的话题——
“杠嘛,都是打在有大龙洞的地方,那里有龙,水大。”
“杠就是龙的脑壳插在龙洞里喝水形成的。”
“杠在龙洞里,用十二把金光闪闪的铜瓢不停的打水喝。”
“杠在喝水的时候,人不能靠近它,靠近了就要把你的脸烧得黑黢黢的。”
“这个地方,偏东雨过后就会打杠咯。”
……
漫不经意地东一句西一句、你一言我一语的一番闲话,反而增加了我对美丽彩虹的一丝丝怯意。长大后有了读书交流机会,才晓得彩虹是雨后空气中细小的水滴,受太阳光反照、折射而成的自然现象。

彩虹是挥之不去的乡愁。在我眼里,她是老家标志性的气象景观,有着不可替代的神圣感。从部队退伍回到家乡工作后,每到秋季下偏东雨的日子,一听到风声、雷声、雨声,就不由自主想起那道彩虹。但令人失望的是,多少次回家都没有看到过她的芳影。到几个乡镇工作,自己也有意识的关注,可惜都未能如愿。
恁长时间,那道彩虹都到哪里去了呢?闲暇时,脑海里就像放录像似的反复呈现当娃儿时老家的模样,意图寻找出个中的蛛丝马迹来——
从猫岩、十字垭、摩天坡、灵官鼎,一直到相邻的前进村的龙头岩,天星村的九拐子、铁炉沟、象鼻绞水,新华村的刀子岩,这一带地方的大地名叫大垭槽,三十多年前可是一片估计面积超万亩的水田啊。春天,梯田里满是乡亲们驱赶水牛犁田、栽秧的身影;夏天,梯田里秧苗葱茏,风不时吹来薅秧的乡亲们,那一塆又一塆、一坡又一坡悠扬的秧(山)歌声;秋天,梯田里谷浪翻腾,一派金黄稻香;冬天,从山上径直往下看,那一汪汪水田就像镶嵌在天地间的千万面镜子,在阳光或月光照耀下泛着粼粼波光。还有那些穿插其间的绿水槽、三叠水、流水岩、响水河、大河沟、马连沟、响水洞、大龙洞、三潮水等数不清的大小溪流、山泉、水渠,那些翠得淌绿的山岗、山丘、山崖。用现在的书面语言来说,大垭槽简直就是一个大大的湿地公园,其壮观程度不亚于现在云南的红河梯田。
秋天偏东雨后的彩虹,就经常出现在这样的地理和生态环境里。以后彩虹不知不觉的走了,恰好起于水田荒芜,森林植被遭砍伐,有的溪流源头改变流向、水量减少比较明显的时期。

赤橙红绿青蓝紫,彩虹的七种颜色。直觉告诉你我,它是天地间的色彩在彩虹上的投射和反映,但更是人与自然共同命运的色彩,值得人们用心去呵护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多少人垂涎于黑山那茫茫的林海。在十弯八拐的乡村公路、羊肠小道,你时常会看到乡亲们起早摸黑砍卖树木的身影。为了躲避林业检查站的检查,他们或肩扛或背负百十斤重的木料,不惜翻山越岭抄小路到几十里远的地方出售。更有甚者,猖獗到用货车偷运木材闯关到外地交易。土生土长的我,每次看到乡亲们那副被木头压弯的身体、那张青筋股股涨红了的脸、那满身泉涌着的汗水,莫名的情绪油然而生。特别当听到他们背负了几十里的木料快到变成现钱而被没收处罚的消息时,更觉酸楚难耐。可一看到风景如画的黑山石笋、石门、狮子峰、鲤鱼河……,在丁丁伐木声中满目疮痍,又感到一种滴血般的痛。
那个时候,我正好是区委机关大院和区委宣传部仅有的“农民工”毛头小伙、重庆日报特邀通讯员,于是便自然想到利用手中的笔,通过党报舆论间接的去阻止这一现象。可一边是父老乡亲的生计,一边是不三不四之人的财路,一边是相关的人情世故,一边是家乡的长远发展,一边是自己“泥饭碗”的临时工身份,让我几次沉重提笔又几次沉重搁笔。经历了好长时间七上八下的内心纠结、冲突、煎熬,最终还是因自己骨髓里涌动着的对这一方水土深沉的爱,使我鼓起勇气采写了反映黑山地区非法砍卖树木的读者来信。当时的报纸只有四个版面,非常金贵,可《重庆日报》第四版,却以近半个版面刊发了题为《决不能再干贻误子孙后代的事了》的记者调查和读者来信。舆论的浪潮卷去了民间那一把把闪着寒光伸向大山的斧头、弯刀、锯子,换来的是苍山蓬蓬勃勃的生机和随风翻滚的林涛声声。
无独有偶,新世纪初,或许因为有点宣传文化工作经历吧,曾经在乡镇工作过的我,被组织再次安排到与文化旅游关联的石林镇担任主要领导。这次很难得的是有机会与乡村的弟兄姊妹们一道,参与了国家具有千秋战略意义的退耕还林还草行动。我们挽起袖子,在风雨和汗水的交织中,一手在坡地、荒山、溪河边大量栽植竹木;一手虔诚地呵护着上苍赐予的那片宝贵森林。
南天门与黑山,同属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的大娄山脉,这里云海日出、林翠花繁,因溪流密布,又名溪源。是重庆主城南部的绿色生态屏障,也是地质上中国成岩最古老的万盛石林所在地。
和大多数山区一样,习惯于靠山吃山、靠林吃林的乡亲们,砍卖树木是最直接、最现实、最来钱的路子。他们发明了不少“合情合理合法”砍卖树木的招数和术语,——大凡什么“风折木”“雪压木”“虫害木”之类的灾损林木,都可以堂而皇之的砍伐、买卖。呵呵,由于初来乍到,开始我也被这套“迷踪拳”“障眼法”给忽悠了。好几次下村路过南天门,看到路边堆了不少等待运出去的树木,我搔了搔头心里纳闷起来,“这段时间山上没听说吹大风啊,哪里来啷个多的‘风折木’呀?”同行的人抿嘴笑着不吭声。之后,镇里一茬又一茬地接二连三开了些土洋结合的治理“处方”,才算消除了这个“慢性病根”。由此, 在白云、飞流,绿树、山花,珍禽、祥兽簇拥下的南天门,越加显得仙气灵动了。
如今,缤纷的大山早已成为山里人家致富的“绿色银行”。日子越过越好的乡亲们,从过去对大山的宗教迷信、矛盾冲突、无节制的原始索取,到现在与其惺惺相惜、和谐共生,这是多么难得的群体性觉悟呀!

秋天偏东雨后的彩虹,终于又烂漫当空舞了。我在想,脚下这块和和润润的土地、周围蓊蓊郁郁的群山、溪涧叮叮咚咚的泉水、碧空悠悠扬扬的云絮、树上脆脆朗朗的鸟语,还有人们呼吸着的清清香香的空气味道,不正是彩虹重现的最好注释吗?
黑山、狮子槽草甸、南天门、鲤鱼河、九锅箐……
徜徉于蓝天云海,纵情于高山流水,我们仿佛听到来自幽长空旷的历史时空隧道里,圣贤指尖上轻轻传来的古琴声声。这是“为天地立心”的福音啊!
哦,偏东雨后,老家那道吉祥的七彩霓虹。


渝公网安备:50010302002751号